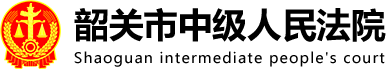担保型买卖合同纠纷的法理辨析与裁判对策
作者:原创 信息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9-06-07 浏览次数:3924 [打印此页 关闭此页]
担保型买卖合同纠纷的法理辨析与裁判对策
近年来,在民间借贷活动中,流行这样一种担保方式:借贷关系的当事人或其关系人在借贷合同之外再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口头约定如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则执行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转让给出借方,以房屋抵债。对这种担保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后让与担保”。[1]因实践中此类案件均是以买卖合同纠纷作为案由立案,故本文将这种以担保债务清偿为目的而签订的买卖合同称作担保型买卖合同,并以此为题展开讨论。因此类担保型买卖合同而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涉及主要争议问题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是什么,是借款关系还是买卖关系;起担保作用的买卖合同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效力如何认定;如何把控案件审理范围,有关借贷的事实是否需要进行审理;如买方(实系出借方)要求履行买卖合同或主张赔偿违约金,如何处理;如买卖合同在起诉前已经实际履行,如何处理。以下试就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本质和效力进行分析,以期还原这一非典型担保的本来面目。
一、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本质
(一)担保型买卖合同本质是清偿期前的代物清偿预约
担保型买卖合同虽然冠以买卖之名,但买卖不过是其借用的外衣,揭开这层画皮,究其实质,是双方预先约定如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则以物抵债,其在民法概念体系中的定位应是代物清偿预约。
所谓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来代替原定给付,从而使原有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合同。通俗地说,代物清偿就是以物抵债。
所谓代物清偿预约,是指当事人在清偿期前预先约定,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或债务人得请求以特定标的物为代物清偿,即以特定之物抵偿债务。[2]其有两个特点:第一,代物清偿预约成立于债务清偿期届至之前;第二,代物清偿预约以债务不履行为停止条件。可见代物清偿预约的机能主要在于预先为债务设定担保,与代物清偿侧重于清偿期后的债务清理大异其趣。
担保型买卖合同符合代物清偿预约的本质特征,因此就是代物清偿预约。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而不得拘泥于所使用之词句。按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担保型买卖合同虽然表面上是以买卖合同的面目出现,但当借款不能清偿而需要执行该买卖合同的时候,买方并不会真的向卖方支付价款,所谓的价款不过是未能偿还的借款及其利息而已。而卖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目的并非履行买卖合同,卖方从来也没有将标的物卖给对方的意思,双方的真实意思都是以物抵债。可见,该买卖合同实质是不履行债务则以物抵债的预先约定,只不过为掩人耳目或出于其他目的而采用了买卖的形式。“代物清偿虽有财产权之转移,然非对此支付价金或转移其他财产,故不得作为买卖或互易”。[3]买卖与代物清偿各有其质的规定性,不能相互混淆,担保型买卖虽有买卖之外形,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代物清偿预约的本质。
(二)担保型买卖与让与担保之比较
担保型买卖是纯以买卖合同作为担保,其与传统非典型担保中的让与担保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相同。
所谓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之清偿,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至担保权人,待债务清偿后,再将所有权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当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4]例如,甲欠乙借款债务100万元,为担保清偿,甲将自己一套房屋的所有权过户至乙的名下,届期如清偿债务,乙应将房屋所有权过户回甲的名下,如届期不能清偿债务,则乙可以就房屋优先受偿。由于不动产让与担保在办理过户登记过程中要征收高额税费,故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动产让与担保的事例并不多见。
让与担保在实务中大抵也是以买卖的形式来完成,这使其与本文研究的担保型买卖(纯以买卖合同设定担保)有相似之处。担保型买卖与让与担保的相同点在于:二者均属于法无明文的非典型担保,其目的都在担保主债务的履行,具有从属性;二者在终极上都是寄望于以担保物的价值受偿;两种担保方式通常都以买卖的面貌出现,而买卖合同本身均非真实意思表示(详见下述)。
二者的区别在于:让与担保是在设定担保时就先将担保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待债务清偿之后,再将担保物所有权转移回担保人,由于债权人在获得清偿之前已经握有担保物的所有权,故属于物权性质的担保;而担保型买卖在设定担保时只签订买卖合同(代物清偿预约),并不转移担保物所有权,是约定待债务不履行时再转移房屋所有权,起担保作用的只是债务人或担保人将来以物抵债的承诺,是纯以买卖合同本身的拘束力作担保,债权人并不享有任何物权性质的权利,因此是人的信用担保,并非物权性质的担保。由于担保型买卖是约定在不履行主债务时才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杨立新教授将其称为“后让与担保”,以与传统让与担保(先让与担保)相区别。
附带说明,传统上还有所谓买卖式担保,也称卖渡担保,是指“以买卖形式转移权利,而信用授予人不复留有其所授信用返还请求之债权,唯信用受取人得返还信用,而收回其标的物。”[5]买卖式担保是广义让与担保的一种,是在设定担保之时就已经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因此是物权性质的担保,与本文研究的担保型买卖(纯以买卖合同作担保)并不相同。
二、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效力
(一)作为外形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通谋虚伪表示
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是名为买卖,实为代物清偿预约,作为外形的买卖合同属于通谋虚伪表示,无效。
所谓通谋虚伪表示,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相互串通作与内心真实意思不符的虚假意思表示,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相互串通缔结的虚假合同。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但如果通谋虚伪表示中隐藏有其他法律行为的,适用关于该其他法律行为的规定。[6]
分析担保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必须区别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买卖合同的意思与作为物权变动结果的所有权转移的意思,分别进行考察。在担保型买卖合同中,如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因素,则双方关于不能清偿债务则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意思应该是真实的,但双方关于引起该物权变动之原因(买卖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引起该物权变动的真实原因是以物抵债的约定,而非买卖合同。从卖方的角度看,其真实意思是如不能按期还债,则把房屋“抵给你”,而不是“卖给你”;从买方的角度,其并没有支付价款的意思。双方没有买卖的意思,只有以物抵债的意思。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所有权转移的效果意思真实,就认为买卖合同也真实。这就如同在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场合,不能因为所有权转移的意思真实,就认为买卖也真实一样,买卖仍是通谋虚伪表示,被隐藏的赠与才是真实行为。
对此,还可以类比让与担保场合下的买卖合同。让与担保通常也是以买卖的名义来完成所有权转移。由于让与担保中的所有权转移是以担保为目的,与买卖系终局性的转移所有权有所不同,故自其产生之初就面临是否为通谋虚伪表示的质疑。在德国、日本早期的判例中,均曾将让与担保认定为通谋虚伪表示,但后来的学说、判例则认为,让与担保属于信托行为,双方当事人是真的希望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因此不是通谋虚伪表示。[7]
笔者发现,在关于让与担保是否属于通谋虚伪表示的讨论中,现有论说大多没有严格区分让与担保中所有权转移的意思与作为其外形的买卖合同的意思,往往是笼统地说让与担保并非通谋虚伪表示,仿佛让与担保中所有的意思包括充当让与担保之外形的买卖合同的意思也是真实的。[8]但实际上,让与担保中并不存在买卖的意思。对此,谢在全先生指出,就让与担保场合下的买卖合同而言,“因地政实务上拒绝受理信托关系为原因之所有权转移登记,致以让与担保为原因之所有权转移,均系以买卖为原因之方式出现。实则当事人间并无买卖之法效意思,可见自登记原因之‘买卖’以观,确系双方通谋虚伪之意思表示,唯其间隐藏有为担保债务之清偿,而信托的将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之让与担保契约。”[9]同样道理,在担保型买卖中,作为外形的买卖合同也属于通谋虚伪表示,无效。而代物清偿预约是被隐藏的真实行为,双方关于债务不履行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效果意思实际存在于代物清偿预约之中。
(二)作为隐藏行为的代物清偿预约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代物清偿预约是担保型买卖合同的隐藏行为,其效力应依关于代物清偿预约的法律规定进行判断。
代物清偿预约是否有效,学者见解不一。孙森焱先生认为,代物清偿预约若约定代物清偿权在债务人一方.,即成立任意之债,应认有效;反之,若代物清偿预约约定债权人得请求代物清偿,则应类推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73条第2项或第893条第2项关于流担保禁止的规定,认定其无效[10](需注意的是,台湾地区“民法”第873条第2项及第893条第2项关于流担保禁止的规定已于2007年被修改。修改后的规定为,“约定于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为清偿时,抵押物(质押物)之所有权移属于抵押权人(质权人)者,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这说明,我国台湾地区已经不再禁止流担保契约)。持反对观点的陈自强教授认为,无论代物清偿权在何人一方,代物清偿预约均有拘束力,当发生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请求他种给付,债务人负他种给付义务,但应参照让与担保,课债权人以清算义务,即将他种给付超过原债权额的部分退回债务人。[11]杨立新教授也认为现实生活中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债务履行的(杨立新教授称之为后让与担保),该担保应属有效,在债务不履行时,担保人应转让担保物所有权给债权人,债权人可就担保物变价取偿或估价取偿,但为避免担保过度,应使债权人负清算义务。[12]
笔者以前也曾认为代物清偿预约有效,[13]但经过实务检验及自我反思,笔者认为自己之前的观点欠妥,应予修正。判断代物清偿预约的效力,不能脱离一国的实定法规定,更不能脱离一国的社会实际。
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没有像有的国家或地区那样明文肯定代物清偿预约。[14]相反,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明文禁止在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中设定流担保约款。在债务清偿期前,当事人关于“届期不履行债务,则担保物归债权人所有”的流担保约款系我国法律禁止的无效约定。而流担保约款的本质就是以债务不履行为条件的代物清偿预约。因此,与其说法律禁止流担保约款,不如直接说禁止代物清偿预约。在此意义上,前述孙森焱教授关于赋予债权人代物清偿请求权之代物清偿预约无效的观点,应予赞同。
从现实情况看,担保型买卖基本都是以房屋买卖的形式来担保民间借贷,其中绝大部分涉及高利贷。而供担保之房屋的价值与债权人未获清偿而又应受法律保护的借款本息之金额相比普遍要高出许多,有的甚至高出两三倍。而且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份担保型买卖合同会约定债权人负清算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认定担保型买卖有效,判令债务人履行买卖合同,无异于鼓励重利盘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在情感上也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无论是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担保型买卖合同所隐藏的代物清偿预约均应认定为无效。
(三)对相反观点的辨驳
实务中有观点认为,担保型买卖(代物清偿预约)既非抵押也非质押,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并不触犯流担保禁止的规定。而担保型买卖中关于不能清偿债务则以房抵债的约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应予尊重。即便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也应由当事人自己主张撤销或变更,即便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也还可以通过课以债权人清算义务的方式找回担保物与债权额的差额,因此债务人有救济途径,法院不应直接认定担保型买卖合同无效。而且担保型买卖并非仅存在于高利贷中,有一些担保物的价值与借贷债权额大体相当,认可这一代物清偿预约的效力也并非不公平。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看问题要看本质。流担保约款的本质是代物清偿预约,而担保型买卖的本质也是代物清偿预约,法律既然禁止前者,当无理由允许后者。我们不能因为担保型买卖在形式上不涉及抵押、质押合同,就认为其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真正为法律所禁止的是代物清偿预约,而不仅仅是抵押、质押中的代物清偿预约。
第二,意思自治的边界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之所以禁止流担保约款,就是因其极易引发利益失衡,故需要从立法上加以规制,这与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必要限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是契约正义对契约自由的必要矫正。对代物清偿预约是规定为可撤销还是直接规定为无效,是立法论如何选择的问题,但在解释论上,不能无视我国关于流担保禁止的规定。即便在立法论上,无效说也更为简洁明快,因为实务中,对可撤销事由的举证非常困难,且行使撤销权有除斥期间的限制,合同被成功撤销的事例并不多见。与其让债务人费尽周章主张撤销,不如直接规定无效。
第三,课以当事人清算义务,固然能缓解当事:人间的利益失衡,但却缺乏契约上或制度上的依据。清算义务不是当事人约定的事项,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内容,那么法官根据什么课以债权人清算义务?或谓:公平原则!然而实际是在找不到依据时,“向一般条款逃逸”。与其适用公平原则课以清算义务,不如直接依物权法流担保禁止的规定认定代物清偿预约无效。而且,从诉讼法上说,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履行买卖合同,而被告抗辩合同无效,双方均未就对价是否公平提出主张。法院如判决原告负清算义务,将标的物价值超过债权的部分返还被告,则该判项既非原告请求事项,也非被告抗辩事项,显然与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不符。根据辩论原则,没有在当事人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
第四,判断代物清偿预约(流担保约款)的效力应该有划一的标准,不能认为担保物价值与债权额基本相当就有效,不相当就无效。如前述,如果认为代物清偿预约有效,则在担保物价值明显大于债权额的时候,会形成实质的不公。而如果认为代物清偿预约无效,则即便在担保物价值与债权额基本相当的场合,也不会产生不公平。因为认定担保型买卖(代物清偿预约)无效,并未否认债权人合法的债权,如债务人自己就是担保型买卖之卖方,则与无担保的债务无异,债权人可通过执行程序就债务人的财产(包括担保型买卖的标的物)获偿。如果是第三人充当卖方,则第三人实际上具有以标的物价值为限提供有限保证的意思(这也是经探求真意,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实质解释的结果),第三人应在标的物价值范围内就债务清偿承担连带责任。[15]如此处理,并无不公平可言。
要强调的是,即便认为代物清偿预约(担保型买卖合同)有效,债权人对标的物也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认定代物清偿预约无效使债权人通过执行程序取偿并不会使债权人地位恶变。有学者认为,担保型买卖合同(后让与担保)创设了一种法无明文的非典型担保物权,债权人对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16]该观点值得商榷。在担保型买卖中,只有名义上的买卖合同,并没有发生任何物权变动,债权人对标的物不可能享有担保物权。即便假定担保型买卖合同有效,债权人也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所谓买卖合同以抵偿债务,其享有的也不过是债权性质的请求权,没有优先受偿效力。而且担保型买卖(代物清偿预约)无法进行外在公示,与成立担保物权所要求的公示原则不相符合,认定其有物权的优先受偿效力,对其他债权人并不公平。
三、基本的审理思路和裁判对策
(一)债权人起诉要求履行买卖合同或赔偿违约金的案型
从实践情况看,担保型买卖合同纠纷多系买方(实际是借贷关系中的贷方或其关系人)作为原告起诉卖方(实际是借贷关系中的借方或其关系人)要求履行买卖合同,有些原告会在诉讼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违约金,而被告则通常抗辩双方并非真实买卖关系,不同意履行。笔者认为,审理此类案件,可循下列思路进行:
1.确定诉争买卖合同是否为担保型买卖合同
如果双力一致认可买卖合同是为担保目的而签订,则该事实即可直接认定。但实践中,很多原告坚称就是正常的买卖,与借贷担保无关,此时需要结合证据来认定事实。
与正常的买卖合同相比,担保型买卖合同普遍存在诸多反常之处。比如在最常见的以房屋买卖合同作担保的场合:合同载明的房价一般比同地段相同房屋的通行价格要低;合同上直接写明原告已经支付了全部或大部房款,但原告往往无法提供全部交款凭证;被告作为卖方本应是收款方,但被告手中却有向原告付款的证据(这实际是被告在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合同约定的内容极其简单,通常只有房屋地址、价款、何时交房、过户等核心内容,而对其他事项大都没有约定,不少合同不足一页A4纸;约定的交房、过户时间(实际是借贷的还款期限)与合同落款的签订时间往往相隔较远;通常都约定如果卖方违约要支付高额违约金,而对买方的违约责任则只字不提;被告手中往往握有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录音显示双方实际系借贷关系。
显然,上述买卖合同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即便原告否认买卖合同与借贷有关,但法官根据既有证据,结合被告抗辩意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通常也能够还原案件事实并形成心证。如果法官已经形成“诉争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对借贷关系进行担保”这一心证结论,则根据前文论述,该买卖合同本质上是法律所禁止的代物清偿预约,可直接宣告买卖合同及其隐藏的代物清偿预约无效。如果法官比较保守,不能认定买卖合同是对借贷的担保,那么因诉争买卖合同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至少也应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买卖合同真实。只要不能认定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则原告无论是要求履行合同,还是要求赔偿违约金,都不能得到支持。
2.清理当事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案结事了是我国民事审判追求的目标。仅仅认定担保型买卖合同无效或不真实只是否定了当事人基于买卖合同而产生的请求权,但并未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对当事人的债务关系进行清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35条第1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据此:
(1)如果双方已经承认买卖合同实际是为借贷作担保,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上述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讼请求改为要求债务人偿还借款本息。如原告同意变更,则诉讼标的和案由发生变化,案件不再是买卖合同纠纷,变为民间借贷纠纷。在民间借贷这一诉讼标的中,所谓的买卖合同(代物清偿预约)只是从属于借贷关系的担保,而且是一种法律禁止的无效担保,在最终的判决中法院应对该买卖合同(代物清偿预约)的效力作出否定评价。需注意的是,如果买卖合同的卖方并非债务人本人,则此时所谓卖方实际是担保人,买卖合同(代物清偿预约)虽然无效,但所谓卖方实际上具有以标的物价值为限提供有限保证的意思,其应在标的物价值范围内就债务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经释明后,当事人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仍坚持要求依买卖合同主张权利,则只能驳回其请求,判决只需对买卖合同及其隐藏的代物清偿预约的效力予以否定即可,对有关借款的清偿问题无需涉及。
(2)如果原告不承认买卖合同是借贷的担保,但法官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是借贷的担保这一心证,此时也应按照上述方法处理。法官应在审理过程中向原告适度披露自己的心证,向原告讲明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按照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如原告不同意变更,坚持依买卖合同主张权利,只能驳回其请求。
(3)如果法官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买卖合同是对借贷的担保,但也不足以认定买卖合同真实有效,这实际是关于借贷担保和买卖的事实均属真伪不明,此时无需依《规定》第35条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直接以证据不足以证实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可。
(二)买卖合同业已履行,债务人或担保人起诉主张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案型
如果担保型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而卖方反悔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则不应支持其请求。担保型买卖的本质是代物清偿预约,其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其成立于债务清偿期之前,容易诱发重利盘剥。而对于清偿期之后当事人所达成的以物抵债约定,法律是不禁止的。比如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此处的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就是约定以物抵债。清偿期之后的以物抵债约定如果已实际履行,就构成代物清偿,原债之关系归于消灭。
担保型买卖合同(代物清偿预约)成立于清偿期之前,本属无效,但如果在清偿期届至之后,当事人履行了该代物清偿预约,则说明在清偿期之后,当事人仍具有以物抵债的意思。清偿期前的代物清偿意思不受法律保护,债权人不能强求债务人履行代物清偿预约;但清偿期之后的代物清偿意思受法律保护,已经履行的,产生债之消灭的效力,不容再任意反悔。因此,这一履行行为虽然表现为是对清偿期前无效代物清偿预约的履行,但在规范意义上可解释为是对清偿期之后有效的代物清偿协议的履行。
需要说明的是,业已履行的担保型买卖合同虽然不能被确认无效,但如果确实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则债务人或担保人仍可主张行使撤销权或变更权,要求债权人将标的物价值过分高于债权额的部分予以适当找回,从而尽量实现利益平衡。
【注释】 [1]杨立新:“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2]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下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3页。
[3]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5页。
[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6页。
[5]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7]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1页。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2页。
[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06页。
[10]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3页。
[11]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1页。
[12]杨立新:“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13]高治:“代物清偿预约研究—兼论流担保制度的立法选择”,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8期。
[14][日]近江幸志:《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以下。
[15]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页。
[16]杨立新:“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
下一篇